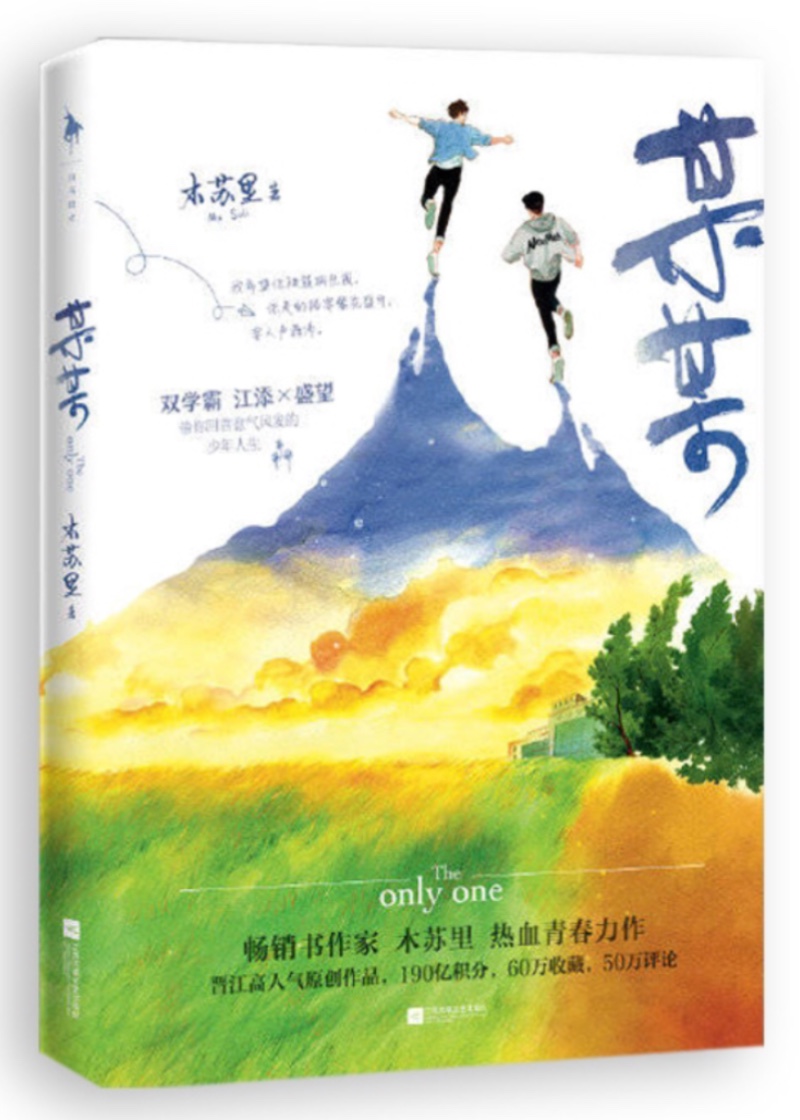漫畫–愛與詛咒–爱与诅咒
奧博相公工睡覺這種憂愁的驚喜, 約會是,早餐也是——此人忙着在微信上口舌,本就拿不動手的廚藝更爲打了折, 顧頭不顧腚。他拿噼啪亂濺的油鍋別無良策, 站在距工作臺八百米的地段, 仗着身長國手長, 拿了個石鏟在那打手勢。
玻鐵鎖着, 廚房煙熏火燎,他眯審察睛眨了半晌才回首來硝煙機忘開了。等到把硝煙滾滾機蓋上緩一口氣,糝和蛋又有點粘底了。
總而言之……成果就很“轉悲爲喜”。
大醫生技產品
江添摁着惦記友好奇心, 在正廳等了身臨其境二不勝鍾。就在他施放無線電話綢繆去廚房看齊的早晚,某人端着盤子帶着孤寂煙火氣來了。
不是勾, 是誠然火樹銀花氣, 江添直接被嗆得咳了兩聲。
他撈過之前節餘的那點雪水喝了一口, 不留餘地地朝盤裡一瞥,表情及時變得有些發傻。
這一貨攤微茫的是個哪傢伙?
江院士話都到嘴邊了, 溫故知新廚師是朋友家望仔,又暗中把刻毒嚥了歸,清了清喉管說:“你這是——”
盛望把物價指數往三屜桌上一擱,強撐着臉皮,用一種委曲求全摻雜着蛋疼的語氣說:“花生醬炒飯。”
重生之高门主母
江添“……”
盛望想說你爲啥寂靜, 但不用問他也明白幹什麼。兩人對着一盤飯愣是出了一股致哀的空氣, 對持幾秒後, 闊少親善先笑了。
江博士立時也不憋着了, 他在盛望笑倒在搖椅的天時指着盤鎮定地說:“我看你不想過了, 拿齒輪油給我炒的。”
“滾,我精研細磨的。”大少爺坐直躺下開始強辯, “我即沒把握好分外量,以孫大姨此次買的辣椒醬顏色稍爲重。”
“來,況一遍。”江添取出無繩機開灌音,“洗心革面放給孫女奴聽。”
盛望沒好氣地說:“我猜猜你在撩架。”
“我不撩架就得吃這個了。”
“吃一口若何了?它看着是慘了點,意外呢?”大少爺本身先挖了一勺,剛出口又一聲不響把勺子拿了出來,神情分外怏怏。
江添忍着笑問:“啥經驗?”
盛望:“呸……齁死我了。”
臨床心理師英文
迄今某人割捨掙扎,懇掏手機點了兩份粥。
從今搞砸了一頓飯,大少爺就變得很既來之,懷抱抱愧。終究他幸這兩天江添能過得要得點子,故此他生米煮成熟飯不做了,當個視爲心腹的情郎。
以前盛明陽在校,他們略爲會稍加流失,而且畢竟是人了,過節冷水性的傢伙都獲位,莫機會單單出門。
他与她的秘密
縝密度,他們都曾在者農村活計過爲數不少年,但尚無有過光明正大的幽期同遊,少年人際安家立業零點一線,來去都在附中那片穹廬間,實屬“能者多勞”,實在沒有實在“不近人情”過。
目前忽地實有大把時分,總想把那幅缺憾漸滿。
盛望說要不然下半晌出門遛?有想去的域麼?
墜淵之
江添取出部手機翻了幾頁,說:“早上有全運會,看麼?”
盛望心說哥,你是否在玩我?
那裡每年新年到元宵都有筆會,着實是歷年最大的權變,但人也是誠多,她們索性是上趕着去送靈魂。只是一點鍾前,他適逢其會決定要做一度乖的男朋友,所以忍着痛決斷地點了頭。
这位alpha身残志坚
但他不領悟的是,江添事實上對酷也不要緊深嗜,單覺得他想出玩,故而本着慣着的心理硬着頭皮挑了一番。
這天夜間的起始就來源於如此這般一場烏龍,誰也沒抱嘻期,還做好了腳被踩腫的未雨綢繆。可當她們真實性站在這裡,在人流人叢中明快地牽入手下手,像方圓浩繁日常情侶千篇一律歡談着、磨磨蹭蹭地往前走,又感覺到再沒比這更允當的選擇了。
經由一片希世的空位時,盛望拽了身邊的人把說:“哥,看我。”
江添扭轉頭時,他扛手機拍了一張燈下的合照。
邊緣是摩肩接踵的打胎,百年之後是顯眼私下的底火,河水十里,從古亮到今,長代遠年湮久。
他想把這張合照也洗下,夾進夫畫冊裡。人間一年四季又轉了少數輪,他們或者在所有這個詞。
沐日裡,繁華一個勁緩緩不散,頗略帶炭火不夜城的情意。兩人面面俱到的光陰一經11點多了。
盛望摘了圍巾掛在玄關鏡架上,咣咣開了一串空調。
“歡歡喜喜嗎?”他問。
江添指着好被踩了不知約略回的鞋:“你覺得呢?”
平凡乙女日記悠遊卡
盛望快笑死了,推着他哥往樓梯上走:“別痛惜鞋了,洗澡去吧江學士。我吃撐了,在宴會廳轉悠俄頃消消食。”
江添看着他星亮的雙目,有轉臉想說點如何,但結尾還擡腳上了樓。他當然知道盛望忙了全日鑑於好傢伙,但他委實久遠沒過過生日了,以至收看年光日趨靠近0點,他的神經會潛意識變得緊繃始,像是一場綿延數年的談虎色變。
說不清是何以情緒,他在衛生間呆了悠久,擦着現已半乾的毛髮在洗臉池邊依偎了不一會。以至於聽到樓下有電話鈴聲,他才驀然回神,把冪丟進微波爐,抓出手機下了樓。
农门娇长媳
他覺着和諧依然故我會有點不快應,但當他在藤椅上起立,看出課桌上格外標格駕輕就熟的透明綠豆糕盒時,他才後知後覺地獲知我不對排除,然則念。
他太想讓前方其一人跟他說句“華誕先睹爲快”了,除去盛望,誰都死去活來。就像個弄丟畜生的稚子寶貝疙瘩,穩住要這樣事物完整無缺地還返回,他才不願跟和氣言歸於好。
“我還找的那家蛋糕店,此次翻糖沒裂了,我視察過。”盛望說。
此次的發糕跟幾年前的色澤很像,但並消失擠擠攘攘擺那多小丑,上頭但他和江添,再有兩隻貓。一隻宓地趴着安頓,那是現已的“營長”,一隻還在玩鬧,那是“旅長”的承。
盛望說:“昔日乾點哪些就喜性拉上一幫人,方今連。”
年齒小的時節怡用謹嚴的詞彙,就連同意都無聲無息會帶上成百上千人。後起他才明明,他萬不得已替大夥許諾底,何時來何時走、隨同多久,他只得也只應該說“我”。
我會陪你過後頭的每張生辰,我會盡站在你身邊,我愛你。
毫秒一格一格走到0點,一齊的現象一如昔日。一如既往這張藤椅,竟然這一來的兩個別。盛望傾身歸西吻了江添瞬息說:“哥,19歲了,我愛你。”
他又吻了頃刻間說:“20歲,我依舊愛你。”
“再有21歲的你。”
……
他每數一年就吻瞬時,從19數到24,從嘴脣到下巴再到喉結,末尾俯仰之間在心口,他說:“江添,生日歡快。”
江添抵着他的額頭,眉心很輕地蹙了一期,不知道是在緩和那種細細聯貫痛惜竟自在相依相剋險阻的心思。
他摸着盛望的臉,偏頭吻去,從親和依戀到賣力,臨了險些是壓着乙方吻到呼吸急急忙忙難耐。
……
她們險乎在睡椅上弄一次,終極藉少數明智進了盛望寢室的更衣室。